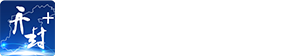折返了的目光——读张富军的画
看者与可见的相互转换,我们再也无法知道是什么在看,是什么被看。——梅洛-庞蒂
在张富军的一些作品中,前景常常有一个直视画面的形象,其目光阻碍了观者的“眼睛”。拉康把立足于主体位置来洞察客体世界的观看称为“眼睛”,但作为观看主体的“眼睛”在面对客体世界的时候,却发现观看的对象以某种方式折返了自己的目光,即受到了来自被看世界的目光:凝视。凝视使原本占据主体地位的观者突然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,意识到自我也是一个可见性的对象,从而破坏了观看的规则,使观者恐慌。
但这种恐慌并不是画者的意图,随着折返的目光,我们渴望去了解目光之人的世界,看他身后的景象,听他想诉说的故事。大面积的灰黑色笼罩着画面,除了前景孤独的人物外,身后暮色侵袭的大地上射出了一柱光,几个人影垂首趋之围观,似朝圣、似悼念……然而,前景的人和身后的事物在画面中出现了对抗,《夜诉》里的她或忧伤的奏乐,或哀怨的望向画外,却不能逃离出来,这个席卷了一切的夜。她的目光折返了观者的目光,观者因为被发现,或者是瞬间地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,而一同被邀进了画中,使观者与夜诉者同在,在抗拒身后一切的同时,观者的主体性发生了变化:他和夜诉人一起感受这让人窒息的夜,接着,这感受开始发散,回放着自己曾经相似的情感,他逐渐认为自己就是画中的夜诉人,于是,观者进入了画中,原来自己就是那个被观看的对象,作为权威的观看者的主体性不存在了,那大概只是曾经的幻象。所以,这也是为何大多数的人看了张富军的画会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。
在他的画中,人物与环境常常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。黑暮似乎是他画面里恒久的底色,人物却是孤离于其中。除了《夜诉》中明显的凝视,在《莫名之光六》中,我们看到画中人在莫名之光的强射之下即将坠落的瞬间,但他突然将头转向了画外,又一次唤醒了观者的在场,这次是在见证他的灭亡。于是我们发现,无论夜幕,还是光,人物都难以适从。再看其他作品,画中人物的眼神并不都是在凝视着观者,也会望向画外,并且这样的形象在同个画面中有时候不止一个,更像是同个形象在画里不同阶段的处境。《伊园之二》中,除了前景中出走的人,中景里也有一个明显的吹笛人,他们都望向画外,相似的容貌让我猜想他们就是一个人,身后仍然是不明的聚众集会。中景里那个着装的吹笛人,也许就是艺术家本人的写照,和身后的众人难以分离,却无法像那些无名者一样虚无的顺从,他望着远方,幻想着出走,并脱下了世俗的外衣。荒凉的山屋、黑压压的枯枝、敏感的飞鸟……无声的诉说着这个应该被离弃的世界,只有出走的路和作为幻象的“我”,才是可以寄托的远方。
画家是在用他的方式表达他认识的世界,以及身处其中的感受。就像画中人一样,他是这个井然有序、理所当然、默默行进的世界中警醒而敏感的歌者,然而演奏的却是远方的理想。他有一系列作品叫做《莫贺延碛》,莫贺延碛是没有生命迹象的荒凉世界的象征,是我们常说的“西域”的起点,传说玄奘在此遭遇了西行途中最为险恶的考验。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着以袍衫,似乎在呼应玄奘经历世间险恶之最,以映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。在这悲歌式的作品里,人物虽然困于其中,没有低迷与妥协,却像是在经历炼狱,画家依然持有信念,那应该是世界的彼岸。
所以,画者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,压抑的画面只是他的言语,怀疑、反思、坚守、信念……这才是他的画里真正的声音。他把观者邀进画中,感受他的感受,让我们用同样不可回避的目光凝视自己及这个世界,在高速穿行的岁月里,这也许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一种方式,折返原本的目光,看向那没有被发觉的“习以为常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