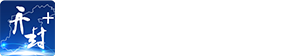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周日。女儿驱车带我们老两口去看黄河,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
好久不见,河的堤坝加宽了,原先平整的路面上有许多纵横交错的车辙印,防汛所需的片石方也不见了。问及一位钓鱼的老先生,他说:“汛期水位上涨,起码有两米多,那些备用的片石全用上了。”能够安然度汛,这是国之大幸、民之大幸,怎不叫人喜笑颜开。我当时那欢愉的模样,恰恰被女儿抓拍到。于是,家庭相册里又多了一张黄河岸边的纪念照。
女儿是个有心人,她在几幅照片上写道:“老爸说好久没看黄河了,路上跟我聊起来他小时候跟同学坐汽马车去黄河滩玩耍的趣事……”
先说汽马车,这是一种用汽车轮子改装的马车,在当年就是最先进、最便捷的交通工具,相当于今天的公交车。我和同学去黄河沿儿玩大都坐汽马车,它就像敞篷汽车,可以随时游览沿途风景。只不过它没有喇叭,马车前头挂有铃铛,听到这响声,路上的小车和行人纷纷让路,当年在马路上跑得最快的就是汽马车。何况票价也不贵,从北关到黄河沿儿8分钱一张票,相当于寄一封平信的价钱。所幸我班的老同学刘炳铸家里是开汽马车行的。节假日买不上票的时候,他就会央求爹爹派一辆专车送我们到黄河沿儿。一路上我们唱着《解放区的天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,抒发那欢快的心情。大堤内那一片沙滩就是我们的游乐场。我们在沙滩上疯跑,一会工夫,那硬邦邦的沙滩就变成了“橡皮滩”,走在上面就像踩在“席梦丝”上。跑累了就躺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。喜欢沙雕的同学就在沙滩上建“楼房”,追寻那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的小康梦……在生活的困顿中,黄河沿儿留下我们青春欢乐的足迹。
而我和黄河的亲密接触是在1952年。那一年我结识了黄河渡口的一位船夫名叫李汩。当年,汹涌澎湃的黄河让人望而生畏。可是,熟悉黄河水性的李汩却在河面上钻浪、坐浪、驭浪,从而在水上漂流。我惊叹他这“独门绝技”,遂拜他为师。初学时,我特别紧张,常常被浪拍到水下,喝两口黄水也是常有的事。师傅便鼓励我说:“别怕,被浪拍打两下,喝两口黄水,这都不算什么,你慢慢就掌握黄河的水性了。”
在师傅耐心的教导下,我终于学会了在黄河上驭浪漂流的极限运动。如今,黄河已风平浪静,再也没有人从事这驭浪漂流的极限运动……
又见黄河,回首往事,往事耐人寻味。